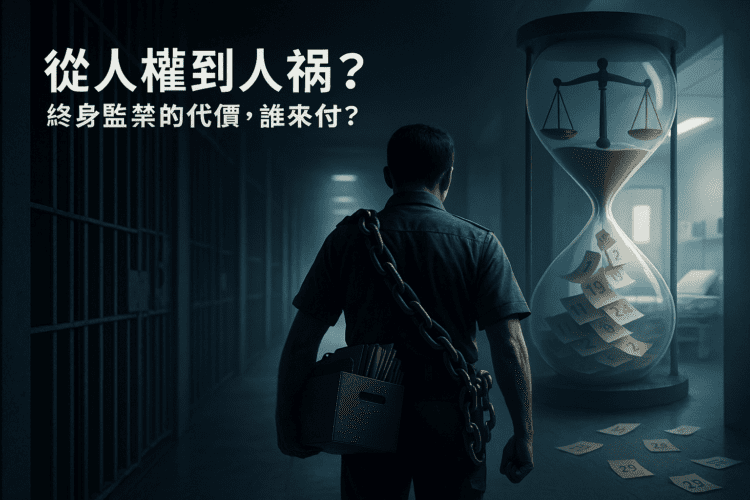【記者范家豪/屏東報導】 2024年,司法院大法官以「有條件合憲」宣告死刑制度仍存在於法體系中。這是一個政治語言上的勝利,也是司法修辭上的平衡。因為死刑判決的門檻高到幾近不可能——必須是「最嚴重的罪行」,再加上「最嚴謹的程序保障」,甚至需合議庭法官一致裁決。實際上,這等於將死刑制度掛在牆上,卻幾乎不會再被啟用。
在這樣的背景下,法務部與藍營立委聯手拋出另一個方案:將無期徒刑劃為三級。第一級——終身監禁,不得假釋;第二級——服刑四十年後才可假釋;第三級——維持現行二十五年可申請假釋。藍委吳宗憲甚至在記者會上高調宣布,司法委員會下週將審議此案。法務部立刻回應:「法務部也提修法版本,與立委版同一方向,甚至更嚴格,含犯殺人罪判有期徒刑10年以上者均不准假釋。可以討論。」
這一套「三級無期徒刑」設計,看似兩全其美:既安撫死刑存廢爭議,又滿足民眾「正義伸張」的情感需求。 但真相是,它既不是正義的勝利,也不是人權的進步,而是一場精心編排的「安撫秀」。它將最棘手、最高風險的問題,乾脆推進監獄大門,丟給基層矯正人員去承擔。
一、司法甩鍋:死刑「有條件合憲」的隱藏成本
死刑仍在,但幾乎不判。社會看似得到了正義的安慰劑,卻無人深思:那些本應判死,卻無法判死的受刑人,將何去何從?答案很清楚——被「重新命名」為第一級無期徒刑者,終身關在監獄裡。
他們沒有明天,也沒有希望。社會以為自己「保留了死刑」,但實際上,是把一群高度暴力、反社會人格的犯人,交給矯正人員日復一日地看守。司法贏了政治平衡,輸了執行成本。最後的承擔者,不是法官,也不是立法者,而是八千名基層矯正人員。
二、藍委的「三級無期徒刑」:漂亮條文,殘酷現實
藍營提出的無期徒刑三級制,第一級不得假釋。這個設計聽起來像是「正義的凜然宣示」,但它更像一個政治標籤:用來告訴社會「我們對重大暴力犯罪零容忍」。
然而,這些犯下重罪的人,大多出於衝動、病態或極端情緒。對他們而言,死刑與無期徒刑,並沒有實質差別。於是,真正的問題不在威嚇效果,而在於監獄管理:這些「永不出獄的人」,暴力只會被壓縮在牆內,變成監獄隨時可能爆炸的定時炸彈。
國外把他們稱為「庫藏犯」,用單人獨居房、一日23小時隔離來消弭風險。但台灣強調人權,獨居不得超過15天,監獄舍房卻仍是多人收容,工場仍需運作。矯正人員沒有任何配套、沒有任何資源,卻要面對一群「絕望無明天的犯人」。這是正義?還是另一種殘酷?
三、監獄的「倉儲化」:司法制度的垃圾場
藍委口中的三級無期徒刑,實際上正在把監獄變成一個巨大的「倉儲庫」。這些不得假釋的受刑人,將從壯年被關到老年。癌症治療、失智照護、安寧病房——所有高齡化的照護成本,都會壓到矯正體系的肩上。
而教育、教化在這些「沒有希望的犯人」身上,已失去意義。監獄行刑法第一條寫著「促使受刑人改悔向上,培養適應社會之能力」。然而,一個不可能重返社會的人,還有什麼改悔與向上的可能?這一切,只是讓監獄逐漸從司法機構,變成沒有一點資源、設施與人力的長照中心。監獄矯治處遇的目的遇到第一級無期徒刑完全走了樣,監獄成了不能教化犯的垃圾場。
四、誰在背後贏?誰在付出代價?
藍委高舉「正義大旗」,法務部巧妙附和。立法者贏得政治掌聲,法務部甩開死刑執行的爭議包袱,司法機關保持了國際人權形象。
輸家是誰?
是每天在高壓環境裡,面對最暴力、最絕望囚犯的基層矯正人員。
是被迫在「人權」與「安全」矛盾中,沒有任何話語權的監獄體系。
是未來必須承擔龐大長照、醫療成本的社會。
五、人權進步,不該以矯正沉淪為代價
社會需要明白,這場「三級無期徒刑」不是單純的刑法修正,而是一個政治性安撫方案。它犧牲的是真實的執行成本,把監獄當成司法制度的掩埋場,把基層矯正人員當成沉默的工具人。
如果立法者真要勇敢,就應該正視死刑的存廢問題,而不是用「不得假釋」來偷渡一個實質廢死的版本;如果法務部真要負責,就應該正視與評估矯正機構的經費、設施、安全、醫療、人力與配套是否皆已完全到位,而不是只用新聞稿回應「可以討論」。
實際上最大的問題是,未經任何的評估驟然修法,輕忽矯正機關當前面臨多重結構性困境:
經費不足,導致硬體設施老舊、更新遲滯;
編制人力長期短缺,使第一線人員超負荷運作;
同時,缺乏足以有效維持監所安全與秩序的司法警察權,僅能仰賴有限的行政管理手段。
此種「財源不足、設施落後、人力匱乏、權限受限」的現實,已使矯正工作承受極大壓力。如何面對第一級不得假釋受刑人,更有第二級要經過40年才得提報假釋受刑人。
我們真的能夠在短時間內蓋幾個大監獄來收容嗎?
人權的進步,不能以矯正的沉淪為代價。
否則,這場所謂「正義的勝利」,只會成為另一場政治口號下的沉默悲劇。
新聞來源:屏東時報